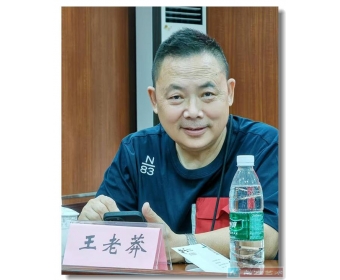地方性写作中的超越性 | 胡中华新诗集《雪落土墙村》出版
|
胡中华,合川人。《钓鱼城》主编,《文旅合川》执行主编,《重庆诗刊》联席主编。作品刊发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红岩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选刊》《草堂》等100余种刊物,获各种文学奖励30余次,入选《中国年度优秀诗歌》等50多种选本。出版诗集《遭遇春天的某个黑夜》(大众文艺出版社)和《雪落土墙村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),以及文化专著《合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》和《江花烂漫》。
胡中华的新诗集《雪落土墙村》,以独特的抒写和风格,刷新了我对中国当代乡土诗写作的认识。他热爱乡土,怀念乡土旧事,抒写乡土人物,关注乡村发展与变化,生发出孤独而浓郁的乡愁。他在写作中,常以谚语、民谣和儿歌介入,不故作高深,不卖弄技巧,风格秀美清新而不落浅俗,机智灵动而充满智性。中华那些短小精悍的诗作,警句如同小春笋不时冒出。比如:“正月的土狗,用它溜黑的嗓子 / 叫开柴门的春天”、“土黄的田埂上,曾经骨折的人 / 携着新的花瓣缓缓归来”、“落花之处 / 黑夜変成黎明”。
海德格尔说:“诗人的天职是还乡,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。”还是在中学生时代,我曾两三次去到中华的老家土墙村,如今差不多30年过去,读到他这本《雪落土墙村》,在往事纷至踏来、远去的山水植物村庄甚至故人眉目清晰起来的同时,不断被他的诗行拨动心弦:“总有一些亲人远走他乡未归 / 我只能将空中的飞燕 / 认成他们”。故乡就像一口老井,中华用他明亮的诗笔挖出清澈泉水,也挖出花椒树一样的疼痛。有价值的写作就是对一个地方持续地回望与观照,才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出生命的本质。故乡没有辜负诗人,诗人也没有辜负故乡。阅读这本诗集,也是每个读者的一次精神还乡,有鸟语花香的宁静开阔,也有锥子已经用熟的尖锐,更有探求生命存在的智慧与救赎的光芒。
雪落土墙村,也落更加阔大深广的土地和心灵。诗人胡中华一直在合川这片富含历史感和现代性的家园生活,情深自不待说,义重更是令人刮目。那么多谣曲由他吟唱,那么多亲人由他爱恋,那么多作坊由他创设……山重水复,春种秋收,“从小到大的爱”,不止于生长,也不止于痴迷。眼中的现实和心中的现实,在诗人朴素、灵动、清新的书写中融通,构成了独属于他的立体小世界和诗意后花园。表达爱不是目的,坚守爱才是理想。真正的好诗,从来都如此。
诗集《雪落土墙村》中,不少体现淡然超然世界观的诗篇,其中充满的机趣和禅趣,是胡中华近来的一大亮点,显现出他的诗歌创作发展方向的多种可能性。中华是迷醉而清醒的乡村歌吟者,万事万物皆在诗行中留影,留声,诸如月亮竹林、桃花苦楝、春秋晨昏之表象,呓语谣曲忧伤之内核,俱澄澈深邃,仿佛长期着力老旧木板上雕刻,刀刀见功力,既深刻精微,又朴拙粗砺,他是当地最好的手艺人。
《雪落土墙村》使胡中华的诗成熟了,有了自己的观照领域,有了自己的话语方式,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,有了别人难以替代的艺术发现。和大多数乡村题材的诗歌不同,胡中华的情感取向值得我们关注。他以自己的发现、自己的情感为基础,为我们留下了曾经的美好,这种获得是丰富的、深刻的、艺术的,是单纯的物质存在所不可替代的。中华以自己的人生阅历、知识储备、艺术素养逐渐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胡中华的诗是一种贴近大地的抒写,当你读到这些鲜活、明亮的诗句时,仿佛闻到泥土的芬芳,聆听到玉米、豌豆和阳光相互碰撞时发出的丁丁当当的声音,引人入胜。在巧妙的叙事中蕴含浓浓的抒情,这种从传统中得来的经验被作者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,我们可以直接从字里行间感知作者的所思,所想,所喜,所悲,所爱,所恨,这种抒情意味,会让读者在潜心阅读中即刻产生共鸣。作者善用比喻,无论是明喻还是暗喻,都准确而生动,显示了诗人对语言良好的把控功夫。胡中华的诗很美,语言美,结构美,意境美,同时有一种音乐美,作者借鉴了民歌和谣曲的表现手法,让诗歌时而整齐,时而错落,读来如大珠小珠落玉盘,常常让人击节称快,这种沿自《诗经》以来的写法,我们读来更感亲切,也与所选的题材相得益彰。
墙是为了隔开,而不是为了分开。而现时中,处处都是墙,有形无形的、高不可跃的、宽不可跨的墙,使人与人真正成为了不好整合的最小单元,不易转化能量的最小元素。近期,看到胡中华的《雪落土墙村》诗集,让我惊喜,给我沉思,引我发问,怎一个乡愁了得。这部诗集里的墙是土做的。土墙是乡邻乡亲们生活所盼、情感所托、精神所依。乡亲们心空里那轮明月的清辉相互映照在土墙上;村口升起的第一声鸡鸣透过土墙可以叫醒山村;炉堂里火焰的笑容通过土墙可以传送温暖……在我看来,胡中华就是一个侧着睡觉的诗人。他一只耳朵向下,听得到种子发芽的声音;他一只耳朵向上,听得懂星星们的话语。所以,他才能写出这样一部乡愁很浓的诗集。
胡中华诗集《雪落土墙村》是一部很厚重的诗集,作者借土墙村这一载体,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故乡的风土人物,那儿有我们的亲人,有我们的温度和热度。在许多人看来,故乡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,它几乎变成了一个概念。但是这本书却像一个万花筒,吸引了我们的目光,让我们透过它看到了乡村的宁静与美好,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善良。我们也读到了作者真诚的内心感受:思古,乡愁,怀旧,团聚,离散,欢乐和疼痛。作者在土墙村寻找自己,那是他肉身和灵魂的发生地,也是他孤独痛苦时常常回望的乌托邦,而我们,则在阅读中寻找自己。毫无疑问,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,都是选择语言在和时间对抗,只有在语言中,我们才有成为胜者的可能。胡中华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。
乡土对胡中华充满了无尽的诗意。他的一再书写,写出了合川与重庆的双重镜像,一则是本原的,另外确实属于灵魂的沃土。返乡和故国一直是中国诗人和世界诗人的共同主题。语言途径的道路就是开往故土的班列,不管是高铁还是动车,本身的速度并不能决定诗歌语言的形成和诗意的完善,反而是重塑语言的责任变得更加明显和重要。诗歌除了主题,其实质是诗人的知识阅历以及人生百态的沉淀,与敏感的语言嗅觉的碰撞而成。诗需要的不仅仅是人生和智慧,在我看来,最重要的是对语言的敏感度、新鲜度和创新能力。胡中华承担起了语言的重担,连接起自己的返乡之路。
地方性写作中的超越性 蒋登科 胡中华是我一直关注的诗人,也是我经常批评的诗人。 关注他有很多原因。我所在的北碚距离中华所在的合川是邻居,他住在渠江、涪江和嘉陵江三江交汇之处,我住在嘉陵江下游,同饮一江水。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经常乘车路过合川,后来是经常开车路过。我去合川的次数很多,因为亲情,因为友情,因为对合川历史文化的兴趣。我认识好几个来自合川的诗人,比如赵晓梦、大窗、李苇凡、胡中华、安卡等等,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,共同特点是对家乡怀着深爱。 我说经常批评胡中华,当然有点过了,其实是朋友之间的关心。中华写诗的时间不短,诗感很好,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说他是年轻的“老诗人”,但我总觉得他的天赋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,写得太少。其实,我有时很矛盾,我对那种天天写,又天天重复自己的写作者常有微词。但是,当有些诗人写得太少的时候,我又为他们着急。中华的理由主要是工作太忙,有时也觉得越写越茫然,好像没有找到理想的发展方向。我“批评”他的理由是,有些事情或许可以暂时放一放,推一推,应该多花一些时间琢磨自己喜欢的诗歌,研究文本,思考历史,浪费了才情实在可惜。才情不是可以长久保留的,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,即使不用,一个人的感受力、表达力也会自然下降。到现在,距离他的诗集《遭遇春天的某个黑夜》出版已经超过了十年。十年啊,在他这个年龄,是多么珍贵的岁月!幸好,他坚持着,而且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色和方向,值得为他高兴。 重庆的诗人很多,一大批70后诗人已经逐渐走上诗坛,拥有了自己的诗路、特色,有些已经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。胡中华也是70后,他的潜力在,他的梦想在,从这本《雪落土墙村》可以看出,他已经跟上来了。“土墙村”是胡中华的家乡,他在那里出生、成长,然后离开,于是就有了回望。这个过程很复杂,中华既是参与者,也是旁观者,但线索只有一个,那就是诗人与家乡之间的生活、文化、精神的关联。 我通过网络搜索了一下,全国至少有几十个叫土墙村的地方。这个非常普通甚至有些土气的名字,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、乡村生活的一种非物质遗存。合川的土墙村在土场镇,更是“土”上加“土”,过去非常偏僻,紧挨着我所在的北碚,现在的交通倒是很方便了。我没有研究过土墙村的历史、文化,不过我相信,在诗人那里,不管这个名字及其代表的文化有着怎样的意蕴,它都是自己成长的地方,在自己的生命深处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最近这些年,中华一直说他在寻觅,在摸索。我猜测,他最终找到的突破点就在这里,就在自己生命起源的地方,就在曾经偏远而如今正在发生巨变的地方,就在城市的边缘而且依然山清水秀的地方,就在他的亲人已经长眠或者依然生活的地方。 乡村抒写在现代诗歌史上是一个普通而又常新的题材,甚至出现了“乡土诗”这样的诗人群落。只是在不同时期,乡村抒写的内涵、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,甚至在不同年龄的诗人那里,也会有很大的不同。中华属于出生在乡村,后来又到了城市的那类人,童年时代接受的文化大多来自山野、田园,以自然、亲情为中心;到了城市之后,虽然环境变了、生活方式变了、心态变了,但他的乡村经历,他对乡村的记忆不会改变,而且成了他的人生底色。于是,他抒写人生的最好方式之一,就是尊重自己的文化基因,以独特的视角不断打量这种基因在人生、现实、情感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和发生的变化。因此,他的乡村抒写和通常所说的“乡土诗”有着一定的差异。 胡中华将诗集分成了“土墙村”“小谣曲”“小亲人”“新作坊”“桃花山”“青竹溪”“小大爱”几个部分,每个部分的作品都不是很多,而土墙村是整部诗集的底色。诗集开篇的《土墙村》是诗人故土抒写的立足点和出发点,从不同角度抒写了自己认识的村庄。他写了村庄的外在形态:
这是典型的乡村景象,尤其是在重庆的丘陵地区,房屋、植物、家畜、家禽、农具等等就构成了一个典型的“家”的形象。不过,如果只写出了这些表象的存在,那是散文的任务,诗人感受的“一日三餐,红白喜事,酸甜苦辣/被土墙围着”,这种折射在诗人心灵上的印记才是诗意,也才是村庄的本质。诗歌意义上的村庄是有人的地方,是有人的生活、人的悲喜的地方,也就是有文化、有情感的地方。 在这首诗中,诗人还写了不同时间、不同季节所感受的村庄:
这是诗人对土墙村生活的进一步细化,这里有母亲,有外来者,有嫂子;这里更有一日晨昏的变化,一年四季的轮回,既写出了农耕文明的特色,也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家乡的细致体验。而且,诗人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段,让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,比如“侧耳时,听到的全都是/谚语一样的狗吠”,这个比喻很特别,谚语是在农村非常流行的一种话语方式,连狗吠都像谚语,这是多么别致的表达;“在春天,你想在土墙村不开花/土墙村决不同意”,“土墙村”成了掌控生命与生机的主体,而不只是一个外在的存在……角度的转换、角色的换位、内在与外在的融合,就让乡村在文字中鲜活起来,站立起来了。 可以看出,中华对家乡的爱是融到骨子里、生命里的。他诗集中所有和故乡、家园、国家、人生、梦想等等有关的作品,都从这份挚爱之中生发出来。他写土墙村的日常生活、人情世故,土墙村人的梦想、追求,涉及到很多话题,涵盖环境、生产、生活、风物,构建了一幅多元且丰富的乡村图景。《土墙村的诗人》很好地揭示了诗人对这片土地的独特体验和情感认知:“我是土墙村旧宅子的诗人/身子又老又旧,而灵魂很新/想法嫩如青枝绿叶”,一开篇就揭示了诗人的心情,在老旧的氛围中,“灵魂很新”,“想法嫩如青枝绿叶”,记忆、怀念与梦想流于字里行间,让人眼前一亮。“我趴在老木桌上写诗/纸上铺着天空,飞花顺窗飘进/落在纸上,自成佳句//我在一个字顶加上浓荫/在两个词间添上流水/在一个感叹号边放出莺啼/让她大吃一惊”,家乡的点点滴滴都在诗人的心灵里生长、升华,再出之以饱满的情感,灵动的语言,建构出新鲜、别致的诗意。而在第一辑的最后还有一首《土墙村》,诗人抒写的却是另外一番感受,“土墙村”成为不断被现代文明冲击的地方,成为连名字也不断变化甚至消失的地方,“从土墙村,到靖林村,再到杨柳村/每一次的撤,或者并,都因你的小/你靠在山边,被遗忘或者不屑/土墙村,早就被别的村庄,别的名字,取代覆盖//行政范围,越来越大/你在别人的眼里,越来越小/小得退回到我内心的某个角落/慢慢隐藏”,因为“小”而不断被取代的故乡,成为诗人心中的痛,最终只能隐藏在“内心的某个角落”。对于社会变迁,这种变化实在算不了什么,但在细腻的诗人那里,每一点小小的变化可能就是根的断裂,就是生命的茫然无依,因此,诗人写道:
从记忆、梦想到失落,再到“欲哭无泪”,蕴含着时代的变迁,隐含着记忆与现实的断裂,勾画出情感与梦想的距离,其间充满惊喜,充满纠结,更充满无奈。 这种变化是个人力量难以抗拒的。但诗人和其他人所不同的是,他可以通过诗的方式还原、保存这些正在消失的美好。因此,在诗集中,胡中华关于土墙村的抒写几乎都是来自记忆的,而记忆与现实的距离,带给诗人的是沧桑巨变,是情感纠结,是对扎根泥土的生命、命运的思索。“小谣曲”写的是对乡村记忆中的一些独特的文化、生态现象的思考,有的已经消失,有的正在消失,但进入诗中之后,它们都将成为诗人以及我们的永久记忆和精神营养。“小亲人”写的是母亲和其他亲人在诗人心目中刻下的印记,诗人的生命、命运和这些亲人有关,他们更是诗人怀念家乡的根源之所在。《静坐中的母亲》中有这样的诗行:“后面是山泉叮咚的小溪/前面是蛙鸣浮动的田野/她的梦境有了几分月色/一条小路,带着泥泞回家/几辈人在坎坷中/为什么,走着走着就不见了?”环境还是这样恬静,但最后的追问却让人备感沉重,这或许就是沧海桑田。时间很残酷,但时间也很公正;变迁是必然的,但当任何一次变迁落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时,那可能都是极其沉重的痛楚!“新作坊”“桃花山”“青竹溪”几辑,依然围绕土墙村展开,以自然、风景、村庄为主线,以沧桑变迁为主题,以诗人的记忆、怀念为手段,抒写了诗人对故土的深爱。《说起某天》有这样的诗行:“一滴,两滴,清脆的鸟鸣,/把我遥远的记忆,从电线上震落。/说起那天,就有一大堆米粒一样的言词/将我淹沒,就有一条暗河,将我围困。/说起那天,黎明就来临,黄昏就来临。”黎明、黄昏同时来临,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啊?“某天”不确指,也可能是每一天。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情感,而是一种复杂、多元的人生体验。在这些作品中,诗人对于朦胧爱恋的回忆,是那么纯真、那么无奈,但也是那么美好。他回忆的对象或许是某个衣袂飘飘的女子,或许是早已远去的两小无猜,但我更愿意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,诗人抒写的是记忆中的包括人在内的那片乡土,以及诗人心中的永恒记忆。 读着这些包含真情、深情的诗篇,我突然获得了一种代入感,仿佛自己也在经历着诗人一样的情感体验、心灵煎熬。从题材到写法,这些作品所关注的主要是一种地方经验、个人经验,但这些经验并不是封闭的,而是以独特的诗句、投入的情感打通了很多和诗人有着类似经历、类似情感的人们进行心灵交流的通道,从而使作品在具有明显的个人性特征的同时,也具有了独特的超越性:超越了自我,超越了地方! 读完这本诗集,我深深感觉到,胡中华不是一个狭隘的诗人,不是一个只生活在自己内心的诗人,更不是一个只关注自我而忽略他人的诗人。他始终与外在世界保持着交流。在《土墙村》的最后,诗人写道:
“土墙村”是真实存在的,但它只是诗人思考乡村变迁、个人命运的一个“点”,而这个“点”散落在中国的许多地方,甚至在所有的中国乡村都有“土墙村”的形象、身影。诗人通过自己的“土墙村”抒写了个人的命运、情感和复杂的内心变化,更抒写了同样处境的中国乡村、来自乡村的中国人的情感与命运,写出了人们的“怀旧、团聚、离散、欢乐、疼痛”,于是才有了“灵魂,闪闪发光”,才有了普视性的“小大爱”,才有了以个人之笔写出许多人情感体验的情怀与胸怀。 胡中华的这部诗集写的是乡村,但诗人并不是迷恋传统的农耕文明,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,或者正在成为历史,而是在抒写自己的生命历程,自己的爱。乡村只是他找到的最合适的依托。乡村的自然、文化可以使人舒放,但诗人不仅是迷恋山水自然,而是在那里找到了真正的自己,至少是找到了曾经的自己。诗人立足的土地是支撑我们成长的地方,但他的梦想、情感、精神并没有受制于小小的土墙村,而是飞升起来,蔓延得很远。诗人写的更多是记忆,是失去,但对于诗歌来说,这何尝不是一种获得?诗人以自己的发现、自己的情感为基础,为我们留下了曾经的美好,这种获得是丰富的、深刻的、艺术的,是单纯的物质存在所不可替代的。 和大多数乡村题材的诗歌不同,在这部诗集中,胡中华的情感取向值得我们关注。“小”是这部诗集最有特色的切入角度,诗人写的是小小的乡村,表达的是小小的情感、小小的痛苦、小小的爱,因为地方性、文化性的加入,这些元素、这些发现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但他的特点是能够在“小”中见大,由“小”及大,由“我”及人,生活化、及物性使他的探索既实在,又拒绝过度依存于“物”。“物”只是这些作品的外在支撑,而“我”始终是这些作品的精神来源。对于家乡,对于土地,诗人没有一味地赞美,也没有一味地批判,而是顺应内心的真实体验,将他所见到的、经历的、想到的,经过内心的熔铸、提炼、升华,挖掘其中的美好,寻觅独特的精神,将传统与现代、回忆与现实、个人与世界、物质与精神很好地融合在一起,虚实相生,内外交融,于是有了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,这就使他的诗和他所抒写的对象呈现出若即若离的美学关系,使他创作的作品能够以精神的方式独立起来,站立起来。 《雪落土墙村》使胡中华的诗成熟了,有了自己的观照领域,有了自己的话语方式,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,有了别人难以替代的艺术发现。虽然我曾经“批评”他,但我不认为他的收获和这种批评有多少关系,而是因为他自己的人生阅历、知识储备、艺术素养逐渐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在诗歌创作中,诗人主体始终都是决定性的。基于此,我对胡中华未来的诗歌探索充满期待和祝福。 2022年1月20日,大寒,草于重庆之北 蒋登科,文学博士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西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,兼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 |
 南方论坛
南方论坛
 频道热门
频道热门
-
鬼金的小说与绘画
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,就像刀子,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,在推进,推进,直到划开皮肤,呈现出白色的茬,然后才是肉,才是红色,破裂的...[详情] -
刘川 译 | 弗兰克·比达特:夜的第四时辰(长诗)
弗兰克·比达特,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《黄金州》与《身体之书》虽获评论界关注,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...[详情] -
清静 |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《三元塔》
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,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,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。其洞察犹如一...[详情] -
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·赖特诗选
美国诗人弗朗兹·赖特,1953年生于维也纳,2015年因肺癌去世,2004年诗集《走向葡萄园岛》获得普利策诗歌奖。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·...[详情] -
马嘶诗选:不与他人同巾器
马嘶,生于四川巴中,现居成都。著有诗集《万古与浮力》《热爱》《春山可望》《莫须有》。曾参加《诗刊》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,获人民文...[详情]